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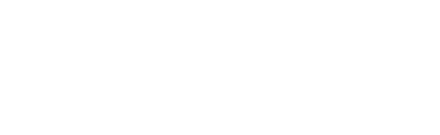

2017年开春之际,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登上《中国戏剧》2017年第1期封面。
本期的《中国戏剧》收录了三篇关于曾小敏的文章,分别是来自《中国戏剧》杂志原副主编安志强的文章《艺术创作触觉》、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罗丽的文章《人淡如菊 静水深流——访粤剧优秀演员曾小敏》和曾小敏的个人感悟《聆听足音》。

《中国戏剧》 2017年第1期 封面
人淡如菊
静水深流
访粤剧青年领军人曾小敏
文·罗丽






人淡如菊
静水深流
访粤剧青年领军人曾小敏
文·罗丽
第一次采访曾小敏是十四年前。当时,她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新秀,在2003年郑州举行的中国戏曲演唱大赛中以一折《投江》获得了红梅大奖。那一年,我写道:“面对众多荣誉和掌声,小敏所流露出来的却是当今年轻演员少有的朴实和谦虚,没有一丝傲气,依旧昨日亲切的邻家女孩。在每次风尘仆仆地下乡演出过后,在走下舞台洗尽铅华以后,曾小敏不是舞台上戏迷簇拥着合照的新星,在她清秀的脸盘上,在那双明亮而清澈的大眼睛里,写满了纯真。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曾小敏,真实低调诚恳的年轻女孩。小敏的温和纯真,如同迎面吹来了清新的风,洗涤了我的心灵。在她眼里,我看到了她对粤剧艺术的执着追求,也看到了粤剧的希望。”
第二次采访曾小敏是2011年,那一年她已经走上了剧团的领导岗位,主演的现代粤剧《青春作伴》在广东省艺术节上获得一等奖。“面前的曾小敏,淡定优雅,散发着母性的温婉,退却稚气的脸庞却依旧真挚、坚定。当年的幸运儿已经长大,如今,她是广东粤剧院青年团的当家人,粤剧新一代的领头人之一。此次采访是在她密集的工作行程中利用休息空档进行的,期间不断有洽谈演出台期的电话打来。一年一度的‘春班’又要到了,粤剧人忙碌的日子开始了。身为剧团当家人的曾小敏自然不会闲着。”
这是第三次,趁着曾小敏携新编粤剧《白蛇传·情》赴京演出的空档,我们俩并排坐在北京冬日的暖阳里,一句搭一句地聊着这些年演过的戏、这些年经历过的事——一如十四年前,我跟随她在寒冬里下乡演出,躺在被窝里聊天一样。多年过去,如今的曾小敏作为广东省剧协的主席团成员,已经成为广东粤剧界青年一代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,但她诚恳又低调的秉性,人淡如菊、静水深流。
艺途寻梦步履坚
说起当时的情形,曾小敏笑着说自己是懵懵懂懂地考戏校,糊糊涂涂地入了粤剧这行。说来也是缘分,虽说从小没有什么粤剧的熏陶,但入学后的小敏居然渐渐痴迷上了粤剧。有了“喜欢”这样的动力,自然也就更加地刻苦自觉了。在枯燥的基本功课上,毯子功、把子功、腰腿功、身段功,乃至唱功,每一样她都学得认真,学得努力。老师上课时教的新动作,她都很快便学会了,从不偷懒,练功毫不懈怠。下了课,在午休和晚修的时间里,小敏总会一个人留在排练场。在别人休息的时间里,粤剧学校的排练场里总有一个身影,在不厌其烦地练着,有时是复习教过的把式,有时是预习和尝试一下没有做过的动作。
厚积薄发,在无数汗水的浸泡下,曾小敏捧回来一系列奖项:1996年参加全国戏校梨园杯大赛,获得中南五省“唱功一等奖”,其载歌载舞表演的《别洞观景》也获得“折子戏一等奖”;1998年参加广东省第二届粤剧演艺大赛,她主演的武打戏《九尾狐仙》获得金奖;2002年参加广东省第三届粤剧演艺大赛中以《投江》再次获得金奖;在2003年郑州举行的中国戏曲演唱大赛中,曾小敏再以一折《投江》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项——红梅大奖。2006年再凭借《放裴》获得2006年广东省第四届粤剧演艺大赛金奖头名。
自1997年从广东粤剧学校毕业进入广东粤剧院开始,曾小敏已经入团整整二十年了。对于她而言,广东粤剧院已经成为她的家。初进剧团,曾小敏获得了一次重要机会——与梅花奖获得者、著名粤剧文武生丁凡合作演出《寒江关》。谁知,这竟然成为了小敏的一次“滑铁卢”。刚刚毕业的她还缺少舞台经验,也是全然不知天高地厚的年少气盛。在她日后写的文章里面这样写到:“才刚崭露头角的我正如初生之犊,自以为凭着自己在戏校的优异成绩,六年来练就的一身扎实的基本功,应付一个《寒江关》绝对没有问题,信心十足。”在南方剧院公演的那一天,曾小敏失手,丢盔弃甲,大败而归。
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,往日里活泼开朗、朝气蓬勃的曾小敏似乎换了个人。她开始对自己失去了信心,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,竟然还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当一名演员,她强烈地感到了在众多前辈面前的自己的渺小和浅薄。惶惶不可终日,屡屡出错,受不住挫折的小敏从高峰落入了谷底,一蹶不振。
曾小敏曾这样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:在看戏的过程中,我练就了对戏文和表演的鉴赏力,也是因为看戏的习惯,让我在一次救场中重拾自信心。那是一次下乡演出,《红梅记》开演第一场,我演完一个小丫鬟的角色,卸了妆,跟往常一样站在幕边看戏。或许是天气过于闷热,中场休息时,女主演突然在后台昏倒了。正当大家焦急得方寸大乱之际,团长大声问到:“谁会演下面的戏?”现场一片寂静,谁也没敢吭声。团长扫了一眼人群,不由分说地向低着头的小敏说:“你马上化妆,上场。”情急中,服装师、化妆师把小敏推进化妆间,左边是打扇的同事,右边是念台词的同事⋯⋯十几分钟后,下半场开演。这场戏在幕边看过十数遍,台词唱腔早已熟记于心,情急之中也忘记了胆怯。救场成功,观众掌声非常热烈,后台的同事们更是一片欢呼⋯⋯
允文允武艺渐深
作为一名刀马旦出身的演员,这些年来,从复排的传统经典作品《寒江关》、《猴王借扇》、《花蕊夫人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山乡风云》到开山担纲的新创剧目《大明悲歌》、《青春作伴》、《梦·红船》、《白蛇传·情》,乃至两次获得广东省演艺大赛金奖的剧目《九尾狐》、《荆钗记》之“投江”、《红梅记》之“放裴”等,曾小敏都十分珍惜,对每部剧目、每个角色都如数家珍。对于自己在舞台上首次担纲的剧目,曾小敏很喜欢《寒江关》里的女主角樊梨花,允文允武,在行当上兼有刀马旦、花旦、青衣,作为性格层次感强、富有表演空间的角色,能让演员演得特别过瘾。
然而,说起最爱的舞台角色,曾小敏首选白素贞。《白蛇传》是她极为钟爱的剧目,赋予演员很大的表演空间,唱做念打都能得到充分的展现。白素贞善良而勇敢,是真善美的化身。情和爱作为人类永恒的情感,不会过时,也更容易得到观众的共鸣。
《白蛇传》作为传统戏,京昆都有上演,曾小敏想,既然婺剧能有自己特色的《白蛇传》,那为什么粤剧不能有呢?她动情地说:“这个戏凝聚了我多年的心力,不求超越经典,但求清雅别致。我期待既能有时代的关照,又不失戏曲的精髓。也许现在的呈现还未能满意,但我会继续朝着理想去努力,希望有一天能创作一个属于粤剧的《白蛇传》。”在创作新版《白蛇传》的时候,她特别重视“情”,希望在作品中能灌入更多的人情味。另一方面,粤剧这个剧种本身就有勇于创新,不断尝试的传统,因此新版特别定名为《白蛇传·情》——特别重视剧中角色情感的体验,在视觉呈现上更为清新。
两个版本的《白蛇传》都是曾小敏的心头爱,旧版本厚重浓烈,新版本时尚清新。在新版本的《白蛇传·情》里,传统戏的游湖、盗草、水斗、断桥的经典唱段和打斗技巧都保有原来的展现空间,但在视觉呈现和心理挖掘上更贴近现代观众。在新版“初见”的唱段里,原来是通过白素贞和许仙相互借物喻情来表达情感,现在则更加注重两个人相见时刹那的心动,放大了两个人心里的感受,可以说比起过往的含蓄表达而言更为直接和细腻。过往表现法海也较为符号化,往往会把法海绝对地反面化处理。站在今天的立场,曾小敏和导演莫非更愿意去相信,没有天生的坏人,有时候人的对立是因立场的不同。因此在新一版的《白蛇传·情》里,都则更着眼于对人物情感的挖掘,尤其是突显出彼此立场不同而对态度的影响。包括法海在内,小和尚、鹤童、鹿童等不再是硬生生的反面角色,而是得到更为人性化的处理,每一个人物都能加入各自情感的解读,他们都被白蛇的一片真情所感动。因此,整出戏用“情”来贯穿,其实也是曾小敏以及导演莫非所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情感慰藉。
在《白蛇传·情》最近一版的修改过程中,曾小敏邀请梨园戏表演艺术家曾静萍老师予她指导,把粤剧版的白素贞细细打磨了一遍。在递伞拒伞那段戏的表演上,原处理上是许仙给白素贞递过一把伞,曾小敏则用手袖轻轻推却。然而,在曾静萍的点拨下,这么短短的一“拒”便更为出彩更为有“戏”——曾小敏依旧轻轻举起水袖,慢慢伸出了纤细而灵巧的兰花指,眼随手送,缓缓地转一圈再伸手一“拒”。那看似小小的变化,实际便犹如特写镜头般被放大,一个细节,一节停顿,牢牢把观众的眼光吸引住了。
除了在传统戏中打磨技艺,演员也通过新编现代戏来锻炼自身对人物塑造刻画的能力。粤剧《青春作伴》是特别为曾小敏量身订造的现代戏,讲述的是一个当代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官的故事。尤其是她饰演的文清,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在外形上都和小敏相当地贴近。但作为当代题材的现代戏,在时间距离上与当下的生活的空间太过于贴近,无论是在人物心理的把握上还是表演程式的运用上都是有难度的。曾小敏过去并不是没有演过现代戏,在经典作品《山乡风云》中,她演过春花、刘琴,那更多是对经典的模仿和承继。“文青”这个角色则是一次从无到有的全新的尝试,没有任何模仿的可能,需要靠演员自己去塑造人物。现代戏难演,如果太过于程式化显得生硬,但如果没有程式,则会显得如同话剧加唱。因此,曾小敏花费了大量功夫和导演沟通,寻找情节恰到好处地去走圆场、亮身段。
在《青春作伴》一剧中,文青的每一段唱、都是经过曾小敏仔细琢磨的;在唱腔处理、运腔技巧方面,小敏根据文青的个性给予一些细微的调整,手法与平时演古装戏时有明显的不同。在音色上,她适当采用了一些流行唱法的特色,让唱腔更接近当代生活味道,适应观众欣赏现代戏的习惯。个性化处理上,她抓住“青春”和“知识女性”两个关键词,着重透过演唱刻画人物身上的青春气息和知性韵味。戏曲唱做念打不分家,在如何拓展现代戏的做功上,曾小敏也下了很多的功夫,像“抗台风”一场,其中很多的舞蹈动作,如表现文青和一众女村民抗洪救灾的“缆绳舞”,就糅合了“串翻身”、“探海”、“前桥”等戏曲程式,亮出她刀马旦的功底。
团长演员一肩挑
曾小敏和《青春作伴》的文青在性格和处事上有着某种高度相似的特质:外柔内刚,看似柔弱,实则坚强,不落套、不随俗、有主见,在经历挫折后通过不断努力取得成功,她是一个平凡而始终坚持自我、在失败和跌宕中逐渐得到认可的时代青年,敢于担起公道和责任。
2005年广东粤剧院拟成立青年团,团内用人聘任更是破格破例,拒绝论资排辈,着力培养年轻队伍,三个团的团长重新竞聘上岗。一直在团内人缘好的曾小敏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下,二十多岁的她脱颖而出,成了青年团的副团长。从一名台前的演员继而成为一位剧团的管理者,曾小敏付出了极多的心力。从演员成为管理者,她最大的感触就是责任重、压力大。刚成立的新团体,没有名角、没有名气,更没有演出市场,一切都要从零开始。如何定位剧团的艺术方向?怎样去占领市场份额?用什么办法吸引青年观众的关注?什么样的作品更具时代气息和表现力?这一系列的问题亟待思考与解决。
曾小敏思索着往事,仿佛十年前的这一段“创业史”还犹在眼前:“第一年的春班演出真的好难,为了让市场接纳毫无知名度的青年团,每个人都耗尽了心血。对于管理和市场毫无经验的小敏,只能从自己的家乡广东三水开始,一个村一个镇那样去拜访,去推介广东粤剧院青年团。”为此,每接一个台口、每演一场戏,都倾尽全力,认真磨戏,千般珍惜、万分投入。经过十年的历练,广东粤剧院青年团的年演出场次突破了110场,曾小敏和她的团队以认真、严谨而富有活力的演出,得到了同行的赞许,观众的好评,新创作的剧目《大明悲歌》、《花蕊夫人》、《青春作伴》、《梦·红船》、《白蛇传·情》先后在全国或省级比赛中获得多个奖项,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,成为热议的话题。
曾小敏的努力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,细数这些年来她获得的各类荣誉:广东省第十次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、广东省直属机关“青年岗位能手”、2011年度广东省“文化系统和行业窗口之星”、第七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、2014年当选广东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、广东省第二届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,广东粤剧院副院长,等等。
然而,面对这一切荣誉,小敏并没有丝毫骄傲,而是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、自己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,她说:“我在一个又一个挫折中成长起来,又不得不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。困难时刻考验人的意志,坚强才是常胜的法宝。我永远记得,红线女老师等前辈艺术家对我的叮咛和教诲。
伶影跨界挑战多
曾小敏触“电”很早,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拍粤剧录影带和出演电视节目的经验,但在电影大银幕上亮相,还是这两年的新尝试。2015年,广东粤剧院拍摄的粤剧电影《传奇状元伦文叙》,丁凡饰演男主角,曾小敏饰演女二号,电影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海南、广西、香港以及澳门等地公映,被列入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。2016年,粤剧电影《柳毅传书》开拍,曾小敏担纲主演女一号龙女三娘,与丁凡再度合作。
作为半个世纪以来最经典的粤剧剧目之一,《柳毅传书》具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和艺术生命力,同时也是考验演员技艺传承的一次历练。对于以前并没有演过《柳毅传书》全剧的曾小敏而言,她感到压力很大:“《传奇状元伦文叙》是喜剧,胡小姐这个角色戏份儿不算太重,演得很轻松。这次《柳毅传书》中龙女这个角色的处理没有那么简单,有层次,有感染力,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打磨。在接到拍电影的任务之后,小敏赶紧把几位前辈不同版本的《柳毅传书》录影拿出来看,从最早的罗家宝和林小群的版本,到倪惠英和梁耀安演的版本,相互比对,总结经验,做了许多案头工作。把整个戏排下来后,又利用了下乡演出的机会演了很多场,为拍电影做了充分准备。”
从舞台到摄影棚,从观众到摄影机,让习惯了舞台表演方式的曾小敏不断在拍摄过程中调整自己:“在舞台上,习惯了和观众面对面,很多情绪上的表演会和现场观众交流、互动,但是在镜头前就不可以这样了,很多时候导演会提醒我:没有观众,不用跟观众交代。演员只需要对着镜头或对手讲说台词。”其次,“舞台上演戏是根据剧情发展一气呵成的,但拍电影是不按情节顺序。有时候先拍一句台词的镜头,没有前没有后的,但演员却需要在短时间内把那句台词的情绪表达出来,各方面的表演也要到位。而且往往同一个镜头需要拍摄几个不同景别,得一遍遍地来。在这样的要求下,演员得到了高强度的锻炼,力求做到导演要求拍哪个镜头的时候,要马上进入那一段戏的情节里面去。”再者,“拍电影要求舞台演员表情和动作更为收敛,拍电影时的内心戏,眼神和表情都不用像在舞台上那么夸张,主要是细腻和准确。这要求演员需要对每一段戏的处理都很细致。”
为此,曾小敏在拍摄前做了许多功课,她把龙女的遭遇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,初遇柳毅时,她是个饱受欺凌需要帮助的弱女子。第二个阶段,柳毅传书后,龙女得到解救回到龙宫,恢复了公主的身份,这时她表现出的是大气、贵气和仙气,对柳毅的深情也是隐隐地去表达。第三个阶段,她化身为渔家女和柳毅重逢,是一个调皮善良的凡间女子。曾小敏说,由于这个角色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格处理,在表演时要注意身份的变化和环境的不同,情感处理要比较细致。
粤剧电影《柳毅传书》是在电影棚内搭景拍摄,拍摄期间曾小敏整整熬了二十天的通宵。和舞台演出不同,拍电影是等待和煎熬的过程,但曾小敏依旧能量满满,一边拍一边看效果,一遍一遍地把角色演好。趁着到片场探班的机会,笔者先睹为快,其中有两组镜头虽短短十几秒,却非常惊艳:一组是风雪中龙女蹒跚前行,曾小敏在规定情境中表达出风雪中的凄苦迷惘与艰难,又不着痕迹地使用了戏曲表演中常用水袖、踱步等技巧;另一组是龙女与柳毅洞房时,曾小敏纤纤玉指轻轻前掀开火红的头巾,调皮而羞涩地转动眼珠左右顾盼,嘴角微弯,把娇羞和喜悦拿捏得恰到好处,细腻美好得让人怦然心动。
短暂的会面过后,我们彼此又各自忙碌,但微信闪动的话语却从未间断。
我问:这些年,无论是困难重重还是获奖无数,你内心最大的动力是什么?
她说:演好戏,做好人。我从跑龙套到小配演到主演再到领衔主演,在反复的挫折和磨炼中,一步步成长。我深深地感受到,要成为一名戏曲演员,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沉淀,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,来不得半点侥幸。
她说:很奇怪,这几年我很少因为生活中的人和事流泪,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理智冷静。但是,我在舞台上哭的次数却越来越多,常常在演出中感动落泪。就好像前几天为《白蛇传·情》走位排练的过程中,我不自觉又完全沉浸在白素贞的境遇里,泪流不止。那个时候,我才发现,原来现实中个体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,都被我寄情于人物之上了。而那个让我抒发情感、宣泄内心的出口,正是我为之不断努力的舞台。原来是舞台赋予了我自由、赋予了我思想、赋予我灵魂、赋予我生命的绽放。
聆听足音
文·曾小敏


聆听足音
文·曾小敏
不经意抖落了儿时的梦,来不及懊悔,也说不上道别,偶然中又已邂逅一片奇异的天空。这里掠过的一切,都是神明般一种存在,这里来往的身影,每给人艳羡、仰视的冲动。这是一片圣地,更是一片朝圣者狂热耕耘的热土。尽管往来者大多是匆匆的过客,却依然不缺匆匆中的永恒。这神奇的方寸之地,叫“舞台”。
台上台下,几步之遥。几步之间,如诗如幻,如泣如诉,那是一个虚幻奇妙的别人的世界;几步之间,嬉笑怒骂,花开花谢,春风秋雨,无数的希冀与幻灭,那是真实的生活。从前明了,这几步看得真切,分得清楚。看得见横于台上台下那堵墙,分得出那些属于所演角色的情感与言语。岁月,模糊了台上台下的界线,仿佛一下子找不到了自己,又好像到处都有了自己的影子。多少次心灵的对话,让我无比震撼。当我触碰着戏里“白素贞”的爱恨缠绵,仿佛置身于西湖边上,与许仙四目相投,怦然心动。金山寺前挥动长袖,这是千般委屈,百般隐忍后无奈的呐喊和抗争。泣别断桥,本是恩与怨的解脱,却始终放不下那魂牵梦绕的冤家,被拖拉着的衣袖,无法挪动的碎步,身随心在抖动⋯⋯此刻,已分不清戏里还是戏外?别笑我呀,时而肆声痛哭,转而又温暖如花!换下一身洁白,再披一袭彩霞,重新惊悚另一种繁华,屏着呼吸,恭恭敬敬,候“她”。“花蕊夫人”的悲愤,“西施”的孤独;异国流落不失风骨的“蔡文姬”,矢志不渝敢爱敢为的“卓文君”,婉约清丽笃定大气的“李清照”,英姿飒爽保家卫国的“穆桂英”⋯⋯一个个跨越时空的女性,忽似故人,款款步来,却宛如流着自己的血,分不清了,到底是自己在塑造角色,还是角色在塑造自己。是生活的点滴教我学会了沉淀?还是角色的替叠让我习惯了思考?脚步虽未停下,慢慢地却便少了许多的躁动与不安,渐多出一份淡定和从容。
是谁偷走了这若远若近的距离?如此地悄无声息。是谁把这异度空间重叠?如此地肆无忌惮。走了二十多年,这小小的碎步,交织着无尽的期盼。恍若隔世的重合,在寻寻觅觅中成就,却原来只是下意识的心灵挪移。也许,生命本质并无彼此,古今中外,人间天上,情感本无不同,虚耶,实耶,哪里分得清,又哪需分清?
都说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,源泉之理,是本,是根。洁白的生命,偶遇缥缈的圣灵,便恍若天衣无缝的撮合,尽管欠缺海誓山盟,仍远胜月老手上那根习惯错系的红丝。
人生与事业,或许是风云际会,是缘分所致。碾碎了无休止的诱惑,屏气凝神,执子之手,不离不弃。听不到号角声声,也看不见旌旗猎猎,只听到一种远方的呼唤,促我前行。行者,不乏鲜花,掌声,喝彩,一路飞歌,一路送迎。只是,遮掩了汗水和热泪的万紫千红,易于把人迷醉,歇下容易,难在知其所止。走过泥泞,坦途不再欣喜若狂,越过山峰,低谷不再顾盼彷徨。保持时刻自醒不易,然昂首之姿,能持。
途中,少不了的风雨雷电。躲闪,苟安,终无缘畅达彼岸。长路漫漫,当知踏步何方,不管足音微茫,用心聆听,定有回响!
艺术创作的触角
看粤剧《白蛇传·情》
文·安志强


艺术创作的触角
看粤剧《白蛇传·情》
文·安志强
我很欣赏粤剧《白蛇传·情》的剧作家(兼导演)莫非用蜗牛的触觉来形容她的创作状态。当她接受了以白蛇传奇为题材创作新剧目的任务时,摆在她面前有两个选择,一是按照通行的版本略加整理;一是另辟蹊径,感受时代的气息,找到自己独特的感觉,创出新意。她说,蜗牛把自己的触角缩在它的硬壳中,日子可以过得很安稳。但她不甘心于这种安逸的生活,于是,蜗牛伸出了触角,四处寻觅,终于嗅到了一种新的感受——情。莫非由此生发了创作灵感,写出了别具一格的《白蛇传》,命名为《白蛇传·情》。
以白蛇传奇为题材的《白蛇传》通行的版本各具特色,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都有一个反封建的主题,白素贞(白娘子)是反封建的代表,而法海则是封建恶势力的代表。其实,这都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所赋予的任务,而白娘子和法海都是不堪重任的。《白蛇传》在“情”字上做文章的妙处就在于剧作家虚构了一对并蒂莲,历经磨难,一瓣投生为白蛇(白素贞),一瓣投生在人间(许仙)。白蛇修炼千年,原是可以成仙的。但她依然恋眷着她的另一瓣,迷恋着人间的美好生活,来到了人间,寻到了她的另一瓣,结成连理,演绎出一段人世间“钟情” 、“惊情” 、“求情” 、“伤情” 、“续情” 、“未了情”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。
“惊情”一场颇具新意。那三杯雄黄酒不是法海让许仙识别人妖给他用的。而是许仙的一片情意。第一盏喝的是在端阳佳节的“一盏柔情觞”,第二盏是为白娘子身怀六甲而饮,第三盏是因许仙表明夫妻二人终老百年的心愿而饮。都是因为一个“情”字,“许郎情真,怎能推搪”,她“为郎甘愿饮雄黄”。结果现出了蛇形,惊吓了许仙,昏死过去。
为救许仙,白娘子来到了昆仑山。与现在通行的版本不同的是,《白蛇传·情》的白娘子到昆仑山不是“盗草”来夺取灵芝,而是“求情”,以“情”来求取灵芝。她以怀孕之身,躲避、抵挡鹿童的攻击,哀哀相求,为了挽救夫君的性命。当鹿童的两支利剑架在她的脖颈上时,她说:“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夫,我生有何欢,死又何惧!”感动了鹿童,放她携灵芝而归。感动鹿童的也是一个“情”字。
饰演白蛇的是曾小敏。90年代初,我曾经观看过她的演出,演的是《荆钗记·投江》一折。那时,她刚刚从戏校毕业。歌舞俱佳,是个文武全才的好苗子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如今已经出挑成一位允文允武的当红主演,她饰演的白娘子,唱做俱佳,论唱,她的嗓音清丽甜润,唱起来情真意切。而她的武功,却又是身手不凡。“伤情”(相当于“水斗”)一场的“出手”开打,一般都是刀对刀,枪对枪,硬器对硬器。曾小敏(白娘子)的“出手”却是双手舞动长袖,只凭双脚,面对飞来的长枪,左推,右挡,前踢,后趟,那双手的长袖,飞舞如旋风,却丝毫未与飞来的长枪纠缠。没有过硬的武功技巧,谁还敢冒这个险?面对白娘子水漫金山寺的举动,法海并没有请来二郎神,更没有祭起金钵罩住白娘子,而是“上呈佛祖,再行处置”,看来,他的心也有些松动了。
“续情”(相当于通行版本的“断桥”)一场的白娘子见到因一念之差到金山寺躲避的许仙,不是一味地对他倾诉衷肠,而是既伤情,又难舍。那烈性的小青追杀许仙,白娘子阻拦,言说是“纵然要分要离,也要和他说个清楚”。及至两人相诉,依然难舍旧情。
毕竟天有天条,人有律条,阴阳相隔两重天。然而,一个“情”字,却冲破了阴阳的阻隔,佛祖准允白蛇,保得真身,再修千年,即可成人。那时,佛陀花开,再续旧情。白蛇之情,说是感天动地,不算为过吧?
说到“情”字,倏然有一闪念:《白蛇传·情》这个剧名,读起来有些拗口。中间那个“点儿”能不能去掉,称之为《白蛇情》。妥否?特此请教方家同人。

 网站首页
网站首页
 剧院概况
剧院概况 演出品牌
演出品牌 演员主创
演员主创 剧目推介
剧目推介 剧院动态
剧院动态